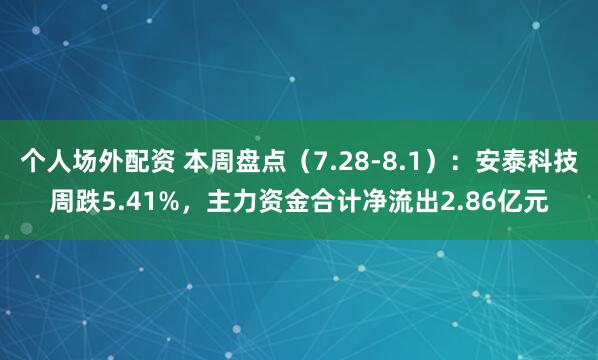*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国内在线配资

同时改善夜间睡眠与日间功能,这款抗失眠新药如何做到?
失眠是最为常见的睡眠问题之一[1],当广大失眠患者数到第1000只羊仍无法入睡时,科学家们正在实验室与失眠的复杂机制博弈,并取得突破性进展。2025年6月20日,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官网显示,一款新型失眠药双重食欲素受体拮抗剂(DORA)达利雷生(商品名:科唯可)正式获批用于治疗以入睡困难和/或睡眠维持困难为特征的成人失眠患者。
此前,达利雷生已于2022年1月、2022年4月、2022年8月、2022年12月、2023年4月分别在美国、欧盟、英国、瑞士、加拿大获批用于治疗失眠,随着该药物在国内再次获批,这款新型抗失眠药物将为全球更多患者带来治疗获益。达利雷生治疗成人失眠患者的中国Ⅲ期临床研究于6月被
Sleep杂志接收,结果表明,达利雷生显著改善失眠患者的夜间睡眠与日间功能,疗效持续,无成瘾性,停药后无戒断反应、无反跳性失眠,在中国患者人群中再次展现出显著疗效与安全性优势 [2] 。 这款靶向双重食欲素受体的新药,究竟是如何突破传统抗失眠药物的局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溯它的研发密码。
研发的起点:失眠症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2017年发表的一项包含17项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普通人群有临床意义的失眠患病率达到15% [ 3 ] ,失眠患者同时存在夜间睡眠和日间功能的损伤,其中日间功能损伤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多重不良影响,甚至可能引发恶性意外事故 [1] 。然而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抗失眠药物治疗过程中仍然存在多种问题 [1,4,5] 。
表1 当前常用抗失眠药物仍存在不足

传统抗失眠药的不足以及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临床亟需一种能同时解决入睡与睡眠维持障碍,同时规避现有镇静催眠药不良反应并能提升日间功能的治疗方案。食欲素(orexin)是一种在下丘脑外侧区域合成和分泌的促进觉醒的神经肽,1998年,有2个独立研究小组在大鼠下丘脑中发现了2种未知的神经肽,分别被称为食欲素A和食欲素B[6,7],其中食欲素A以相似效力激活食欲素1型受体(OX1R)和食欲素2型受体(OX2R),而食欲素B则优先激活OX2R[4]。在睡眠-觉醒周期中,食欲素受体与食欲素结合可以发挥调节睡眠-觉醒状态的作用,当夜间食欲素分泌过多时会导致觉醒系统过于强大,不能顺利切换成睡眠系统,机体出现失眠[4]。这使食欲素受体拮抗剂在治疗失眠症方面表现出巨大潜力。
食欲素受体拮抗剂根据其结合亲和力可分为选择性OX1R拮抗剂(SORA1)、选择性OX2R拮抗剂(SORA2)和双重食欲素受体拮抗剂(DORA)。近20年来,国内外医药研发机构针对食欲素受体研发了几十个化合物,发现SORA1并没有明显改善失眠的效果,部分SORA2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强大的催眠作用,但仍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而DORA具有良好的抗失眠效果和安全性,在过去10年成为新型抗失眠药物研发的主要方向[4]。
先导化合物的结构优化之旅:从海量筛选中成功突围
新型DORA由于存在剂量残留效应,且缺乏改善日间功能的循证依据,为进一步优化DORA类药物的药理学特性,进一步提高其抗失眠的疗效和安全性,Idorsia制药公司研发了一种新型DORA化合物——具备快速诱导睡眠、整夜维持睡眠、无残留效应且改善日间功能等特性[8,9]。
▌初筛阶段:沧海拾珠
研发团队最初通过Ca2+释放实验开展高通量筛选,最后从46种化合物中选择了ACT462206(第7号化合物)[10],其在转运蛋白特性、蛋白结合率、代谢稳定性、酶抑制特性、药代动力学方面均展现出优秀特性,并在大鼠和犬类模型中发现ACT462206能延长快速眼动(REM)与非快速眼动(NREM)睡眠时间,并保持睡眠结构完整[8]。

图 1 先导化合物ACT462206(第7号化合物)
▌优中择优:多维雕琢
结合失眠治疗需求,对化合物的进一步优化重点在于短半衰期(避免次日残留)与高脑渗透性,结合大鼠和犬动物模型体内药理学实验及体外ADME(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特性评估,研发者最后共筛选出20个候选化合物,从中选定临床前研究对象,并对是否符合理想失眠药物的药理学特性进行严格的评估,最终三种候选化合物(ACT-541468、ACT-658090及ACT-605143)突围而出[8,9]。
▌精益求精:面向临床需求的改造
研究人员随后采用雄性大鼠模型对三种候选化合物的促睡眠作用进行研究。ACT-541468展示出了显著优势:与对照组相比,觉醒时间减少22%,NREM睡眠与REM睡眠时间分别增加29%和84%;持续NREM睡眠潜伏期缩短59%(P=0.0002),REM睡眠潜伏期缩短58%(P=0.0006)。且剂量效应研究显示,ACT-541468能剂量依赖性地改善睡眠/觉醒参数,表现为主动觉醒时间减少,NREM与REM睡眠时间增加[9]。值得注意的是,该化合物在延长两种睡眠时相的同时保持了生理性睡眠结构比例[8]。
为了排除化合物在不同种属间表现出显著的分布与清除差异,研究者还引入基于生理的药代动力学-药效学(PBPK-PD)模型进行跨物种药代动力学研究,预测该化合物在人类中的药理学参数。结果显示,ACT-541468在模型中显示出最快的模拟口服吸收速度和较短半衰期*,人类模拟数据还表明,ACT-541468能快速达到较高的食欲素受体占有率峰值,且受体占有率下降迅速[9]。
*注:Cmax:血浆峰值浓度,tmax:达到Cmax需要的时间,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Cmax能使睡眠迅速开始;终末t½:药物终末消除阶段血浆浓度下降50%所需的时间称为终末半衰期,达利雷生约6小时的终末半衰期可确保:1)整夜睡眠维持所需的药物覆盖时长,2)晨醒时药物暴露量较低,从而有效降低次日残留效应风险;AUC:血浆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如AUC0-∞)反映药物在体内的总暴露量,可用于评估生物利用度和清除率。
基于上述临床前研究结果,ACT-541468(化合物93)被选定进入临床开发阶段,最后被命名为达利雷生(Daridorexant)。
独特机制优势与稳扎稳打的循证积累:达利雷生在新药研发之路上成功突围
与传统镇静失眠药物的作用机制不同的是,达利雷生选择性靶向结合OX1R和OX2R,并对两种受体具有均衡且高度选择性的拮抗作用,通过阻断食欲素系统,抑制过度觉醒,从而促进恢复性睡眠发生,且不会影响睡眠结构[11]。这也使其在接下来的临床试验中表现十分出色。

图 2 达利雷生作用机制
针对达利雷生,研发者共开展该药物治疗失眠障碍临床试验研究22批,纳入受试者4036例,其中Ⅰ期临床试验18批600例;Ⅱ期临床试验3批778例;Ⅲ期临床试验3批2658例[12]。
表2 达利雷生临床试验结果

*注:IDSIQ是首个经美国FDA指南验证批准的由患者自评的日间功能评估工具,关注日间功能的警觉/认知、情绪和嗜睡这三个关键域,评分越高意味着日间功能损伤越严重[18]。
基于以上疗效与安全性证据,达利雷生已获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批准用于治疗慢性失眠,并且是目前欧洲唯一获批的DORA,在国际/国内失眠指南中均推荐达利雷生作为失眠治疗的首选用药(IA)[20-23]。从指南中可以看到,达利雷生早已被我国失眠指南明确推荐,本次该药物在国内获批,极大提升了中国失眠患者的用药可及性。作为兼具夜间疗效与日间获益的DORA类失眠药物,其在中国市场的商业化落地,标志着我国失眠治疗正式迈入精准调控“睡眠-觉醒”开关的新阶段。

图 3 国内外指南共识一致推荐达利雷生为失眠的一线治疗药物
结语与展望
双食欲素受体拮抗剂(DORA)作为新一代抗失眠药,避免了镇静催眠引发的副作用,通过抑制过度觉醒,促进睡眠。达利雷生作为新型双食欲素受体拮抗剂,通过选择性调节觉醒-睡眠通路,填补了慢性失眠治疗中“有效且安全”的需求,其药代动力学特性和循证数据支持其在失眠患者中兼顾夜间睡眠和日间功能改善获益,且长期安全有效应用,为失眠管理提供了新的治疗范式。
达利雷生中国III期研究结果登上国际睡眠领域top期刊Sleep,以可靠、详实的数据证实了达利雷生在改善中国失眠患者睡眠质量上同样展现出显著优势,且维持了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特征。二十年磨一剑,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从分子设计到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达利雷生的研发历程凝聚了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这二十年间,研发团队夜以继日攻克技术难关,最终交出了一份循证证据完整、疗效确切、安全性卓越的答卷。如今,达利雷生已成功实现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跨越,其上市不仅代表着中国创新药研发实力的提升,更承载着为广大失眠患者带来“自然好眠”的使命与承诺。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24, 57(6): 560-584.
[2] Huang Z, et al. Sleep, 2025.
[3] Cao XL, et al. PLoS One, 2017, 12(2): e0170772.
[4] 于景娴,等.中国合理用药探索,2024, 21(2):20-25.
[5]Sanofi-Aventis US, LLC; Highlights of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Ambien CR (zolpidem tartrate) [package insert]. 2022. Available from: https://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22/021774s021s025s028lbl.pdf (accessed December 2023).
[6] SAKURAI T, et al. Cell, 1998, 92(5):1-696.
[7] LECEA LD,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1998, 95 (1) : 322-327.
[8] Boss C, et al. ChemMedChem. 2020;15(23):2286-2305.
[9] Treiber A, et al. J Pharmacol Exp Ther. 2017;362(3):489-503.
[10] Boss C, et al. ChemMedChem. 2014 Nov;9(11):2486-96.
[11] Muehlan C, et al. Eur Neuropsychopharmacol 2019;29:847–57.
[12] 陈本川.医药导报, 2022(009):041.
[13] Muehlan C, et al. J Clin Psychopharmacol. 2020;40:157–66.
[14] Muehlan C, et al. Clin Pharmacol Ther. 2018;104:1022–9.
[15] Muehlan C, et al. Curr Drug Metab. 2019;20:254–65.
[16] Dauvilliers Y, et al. Ann Neurol. 2020;87:347–56.
[17] Mignot E, et al. Lancet Neurol. 2022;21(2):125-139.
[18] Hudgens S, et al. Patient, 2021,14(2):249-268.
[19] Kunz D, et al. CNS Drugs. 2023;37:93–106.
[20]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 2023 Oct 18.
[21] J Sleep Res. 2023;32:e14035.
[22] 中华神经科杂志 2024 年 6 月第 57 卷第 6 期.
[23] 中国失眠障碍诊断和治疗指南(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此文仅用于向医学人士提供科学信息,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启远网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